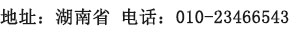封面新闻记者谢颖寻路古蜀道,探秘米仓山。近日,封面新闻“寻路蜀道”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团队再走米仓古道,距离上一次“重走古蜀道”大型采访活动,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。这一次我们决计不走寻常路,直抵米仓山腹地,一探鲜为人知的“米仓秘境”。大山苍茫,前路难测。南江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了宝贵支持,推荐孙凯专家作为我们此行的向导。初见孙凯,我内心不由犯了嘀咕:秋雨连绵气候寒凉,城里年轻人都已穿上了外套,但他好像还未从夏季走出来,依旧一件单薄的短袖。看他年纪已近六旬,个头不高、脸庞瘦削,身材也极为单薄。这样一位貌似不大靠谱的人,能行么?孙凯也许从我们脸上读出了疑虑,但他没有任何表示,乐呵呵地向我们推荐相关线路与点位。在车上,我们提出一些问题,他极为诚恳地作答,但话语都比较简单,没有我们所期待的“言无不尽”,疑虑不由得又深了一层。到达两河口,连日阴雨,导致河道内原本清晰的古桥桩孔已被浑黄的河水淹没,孙凯凭借记忆,逐一指点桥桩孔所在位置。到达寒溪河,他以不太流畅的语言,再现两千多年前那个雨夜,因为寒溪河水位猛涨,萧何得以追上韩信的故事。第二天出发前往巴峪关,雨势更大,气温愈低,“上山路难走,可能要爬两个多小时。”孙凯乐呵呵地提醒我们。究竟有多难呢?他未进一步说明。穿越一片绿草成茵的开阔地,林地间,不时见到正在悠闲觅草的牛羊,小溪蜿蜒向远处延伸,沿溪上行半个小时,终于到达山脚,抬头仰望,云遮雾罩,山不见顶。开始爬山了,泥泞的小路十分湿滑,愈往上走,山势愈发陡峭,渐渐地就没有了路,我们一手撑伞,一手抓住路边的草木借势攀爬,孙凯则远比我们轻松,瘦削的身材灵活地辗转腾挪,手中的一根长棍时而作拐杖,时而为我们扫清草木上的露水,一行人都跟不上他的脚步。“这是什么树?你们认识么?”孙凯突然驻足,指着灌木丛中卓然而立的一棵树向我们发问,大家胡乱猜测一番后,他告诉我们,别看它不起眼,它可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——黄杨木,“好几年没上来,明显长高了。”孙凯感叹。手忙脚乱中,身子渐渐热起来,我们脱掉的外套成为负担,孙凯则更显洒脱。钻过灌木丛与荆棘,一小段比较规整的石板路出现在面前,潺潺的流水沿着石板路淌下来,经年累月,石板被覆盖了厚厚一层青苔,未被完全覆盖的地方,则可以看到被磨得十分光洁的表面。孙凯介绍,这是南江境内一段原汁原味的古道,20世纪90年代,这条路尚有人行走,山下大坝的村民要到陕西汉中的小坝镇赶集,就要翻越这座山,后来旅游业渐兴,交通条件大为改善,大坝成为旅游热点,村民们出山不再走山路,古道就彻底沉沦于岁月的烟尘中。走过这段石板道,前方又没了路,孙凯也要短暂停留辨别山势,经过好几个“之”字形回转后,终于接近山顶,天光渐开,雨雾迷蒙中的巴峪关就在前方,其轮廓清晰,但与想象中的“雄关”似有差距。海拔米的巴峪关到了关楼之下,心中敬畏油然而生。史书记载,米仓古道开凿于先秦时期,明代嘉靖年间,在海拔近米的大山之巅,建起这座一脚踏川陕的关楼,一边是川北,一边为陕南,城墙开了关门,关门上还有望楼,五百年来,兵家、商旅络绎不绝。已被青苔完全包裹的拱形关门,仿佛一座时空隧道,穿行其间就是穿越时间,从先秦出发,经历秦汉、宋元明清,一直到今天。年,孙凯与考察米仓道的专家首次登顶巴峪关。回望来时路的艰难,一行人唏嘘不已,“不登巴峪关,不知蜀道难”,但对于孙凯却轻松平常,加上这一次,他已经十次登顶巴峪关。印象中最深刻的当属年冬季,在漫天飞雪里,孙凯陪同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路登攀,山上白茫茫一片,积雪最深处淹至大腿。专家们在巴峪关待了2个多小时,为古老的关楼做了一次详细的“体检”。上山容易下山难,我们到了山下,双腿已酸软不堪,到了一家饭馆,大家都凑到火炉前取暖,单衣薄衫的孙凯却不肯凑闹热,我们都在惊叹,他瘦小的身子里,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?他依旧乐呵呵地说,“我爬山几十年,习惯了。”晚间,孙凯向我们讲述了他与米仓古道的缘分。20世纪80年代,他大学毕业之后,分配到县图书馆工作。年轻好动,思维活跃,又写得一手好字,南江县博物馆馆长找到他,问他愿不愿意换一份工作,孙凯当场答应了,年,大学专业与文博、考古无甚交集的孙凯,身份从图书管理员转变为县博物馆馆员。“农民勤种庄稼才吃得饱饭,文博工作就是我的饭碗。”农家出身的孙凯吃得苦,他查阅资料,努力探寻每一件馆藏文物背后的信息,野外调查、文物普查总是冲在最前头,渐渐地摸到了门道。年,他通过县志了解到巴峪关信息,在当地采山药的群众带领下,首次登上了神秘的巴峪关,彼时,虽然南江境内不断有文物被发现,但直到年全国文物“三普”,米仓古道都还没有被作为独立单元进行专门研究。年,省考古研究院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巴中行,通过仔细梳理馆藏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内在逻辑,逐渐建立起了线性概念,由东、中、西三条主线所构成的路网逐渐清晰起来。专家们惊异于米仓古道的系列重大发现,直言“米仓古道的价值被严重低估”。孙凯(图左)在查看碑刻摄影:曾业沙河镇红光村石板河,周围区域称米仓古道中线上的“宝藏”,有保存完好的古道、古桥、碑刻、摩崖造像。我们从县城出发,一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。青石板铺筑的古道已罕见人迹,四座碑刻风化严重,又加上苔痕覆盖,难识本来面目。孙凯为我们讲明每一座碑刻的年代及碑文内容,他用指甲抠掉表面的青苔,再用手指头细摩,碑文内容逐渐显现出来,与其讲述不差分毫。他的专注与专业,打消了此前对他的疑虑,同时内心生了一份愧意。从事文博工作33年,孙凯用脚步丈量米仓古道南江境内的所有路线,走过了米仓山的众多沟壑,曾在大山里迷过路,还遇到过多次险情。对于米仓道的线路、重要点位及考古成果,就像自己手心里的掌纹一样熟悉。但他谦虚地表示,专家的称谓不敢当,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博工作者。他很庆幸33年的那次选择,正是这个职业,磨掉了自己的锋芒,培养了“不染不争”的心性,能够静下心来干一辈子自己最喜欢的事。同时,他也高兴地看到,近些年米仓古道研究的不断深入,让名满天下的南江红叶更具魅力,历史文化的赋能,让南江乃至巴中旅游产业无限可能,这正是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。没有名声响亮的专著,也不善于言辞表达,有的只是年复一年地行走。茫茫人海里,孙凯太过于普通,大腕云集的文博界,他也默默无闻。文物无声,但其内在密码永远研究不透,一位基层文博工作者的价值,永远不该被低估。诚如巴中知名米仓道研究专家汪信龙所言,正是孙凯等一大批基层文博工作者,为米仓道乃至古蜀道研究提供了最宝贵支撑,没有他们“坐冷板凳”的精神,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,没有他们一线摸底、发现、保护和基础性研究,何谈更深层次的研究?正是一代代基层文博工作者的持续接力,也才有了米仓古道的今天。古蜀道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,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。坐得了冷板凳,耐得住寂寞。“不染不争”的孙凯如此,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该如此?